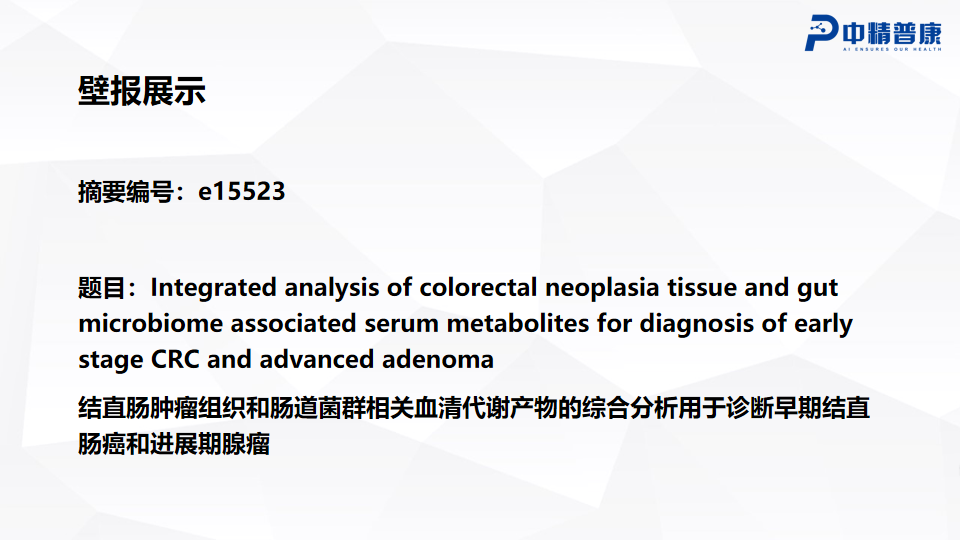線下的脫口秀演員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脫口秀大會(huì)》第四季播出后,延續(xù)了以往的“熱搜”體質(zhì),每期節(jié)目播出后,都要貢獻(xiàn)兩三個(gè)熱搜。
那些曾經(jīng)的素人脫口秀演員,經(jīng)過(guò)幾季的精彩表現(xiàn),收獲大量粉絲,成為了像明星一樣的存在,代言接到手軟,綜藝節(jié)目里常駐,用李誕的話來(lái)說(shuō)“在上海橫著走”。
但線下的脫口秀演員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搜狐娛樂與三位脫口秀演員對(duì)談,了解他們?cè)谛袠I(yè)快速發(fā)展的這幾年,所面臨的機(jī)遇、迷茫或困境,他們中有月薪幾千塊,擅長(zhǎng)講“窮”的重慶脫口秀演員郎飛鴻,也有一邊做微商一邊圓自己脫口秀夢(mèng)的34歲脫口秀演員媚兒,還有入行三年多就已經(jīng)是脫口秀俱樂部老板的北京脫口秀演員楊梅。
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脫口秀行業(yè)是個(gè)英雄不問出處的江湖,大多數(shù)人憑著興趣入行,入行門檻很低,但出師很難,他們大多拿著月薪幾千塊的工資,因?yàn)閴?mèng)想堅(jiān)持著,終極目標(biāo)是登上《脫口秀大會(huì)》的舞臺(tái)。
“鐵飯碗員工”“影視宣傳”“保險(xiǎn)公司講師”
脫口秀江湖英雄不問出處
李誕曾說(shuō),“每個(gè)人都可以當(dāng)5分鐘的脫口秀演員”。
在《脫口秀大會(huì)》的舞臺(tái)上,我們認(rèn)識(shí)到了“銀行柜員”、“車間女工”、“癌癥生物學(xué)博士”、“上海交警”等身份各異的脫口秀演員,而在線下,全國(guó)幾百上千個(gè)脫口秀從業(yè)者,大多也來(lái)自不同行業(yè)。
郎飛鴻、媚兒、楊梅三人就是其中的一員。
在成為脫口秀演員之前,郎飛鴻有一份正式穩(wěn)定而又體面的“鐵飯碗”工作,但因?yàn)?ldquo;享受舞臺(tái)、燈光、粉絲熱烈反響的感覺”,他放棄了父母眼中的這份好工作,一頭扎進(jìn)了脫口秀這股熱浪中。
喜歡脫口秀這件事,在郎飛鴻身上由來(lái)已久,《壹周立波秀》《金星秀》《今晚80后脫口秀》這些國(guó)內(nèi)僅有的幾檔脫口秀節(jié)目,他是忠實(shí)觀眾,但苦于沒有入行渠道,從前只能當(dāng)個(gè)觀眾,后來(lái)隨著《脫口秀大會(huì)》的熱播出圈,線下劇場(chǎng)越來(lái)越多,郎飛鴻在同是脫口秀演員朋友的帶動(dòng)下,正式踏入了這個(gè)行業(yè)。
34歲的媚兒常被朋友說(shuō)有一個(gè)“有趣的靈魂”,所以當(dāng)她看到那個(gè)叫“扯館兒”的喜劇社團(tuán)在招聘喜劇演員時(shí),就勇敢地去面試了,“他們也覺得我特別搞笑,我就加入了那個(gè)社團(tuán)”。后來(lái)隨著脫口秀越來(lái)越火,社團(tuán)把脫口秀業(yè)務(wù)獨(dú)立了出來(lái),成立了“言味兒俱樂部”,媚兒也成為了一名正式的脫口秀演員。
此前的媚兒,做過(guò)保險(xiǎn)公司的講師,自主創(chuàng)業(yè)過(guò),但并未受過(guò)喜劇相關(guān)的培訓(xùn),不過(guò)脫口秀行業(yè)就是這樣一個(gè)英雄不問出處的“江湖”,“我們那個(gè)俱樂部的脫口秀演員,各行各業(yè)的人都有,公交車司機(jī)、監(jiān)理、新媒體運(yùn)營(yíng)等,脫口秀這個(gè)行業(yè)目前來(lái)說(shuō)沒有門檻,你只要好笑就可以了。”
相比郎飛鴻和媚兒,楊梅在接觸脫口秀之前有過(guò)一些舞臺(tái)經(jīng)驗(yàn),是大學(xué)時(shí)期的文娛積極分子,加之外放的性格,“不怯場(chǎng)、有一套自己的表達(dá)風(fēng)格”,這些性格優(yōu)勢(shì)讓她很快走上了脫口秀的舞臺(tái),但單純的舞臺(tái)表演和讓臺(tái)下觀眾能夠產(chǎn)生密集的笑點(diǎn)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我起碼有一兩年的時(shí)間都花在如何解決這個(gè)問題上,有點(diǎn)沒開竅。”
楊梅遇到的問題,其實(shí)也是很多脫口秀新人都難以避免的困境——入行門檻低,但出師難。
“脫口秀跟其他藝術(shù)形式不太一樣,像相聲、評(píng)書都有很多技巧在里面,大家可以從小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但脫口秀沒有,所以這行入門雖快,但想學(xué)精特別難,不少人進(jìn)來(lái)后會(huì)很迷茫。”郎飛鴻說(shuō),“入行三個(gè)月可能就會(huì)刷下一大波人,從講開放麥到上真正的劇場(chǎng)正式演出,一旦一兩次沒有得到觀眾的認(rèn)可,可能他就不會(huì)再上臺(tái)了。”
郎飛鴻透露自己第一次講脫口秀的時(shí)候現(xiàn)場(chǎng)很炸,這給了他很大的自信心,但也有滑鐵盧的時(shí)刻。有一次演出,他感覺自己怎么講都不好笑,現(xiàn)場(chǎng)氣氛非常尷尬,準(zhǔn)備好的內(nèi)容講到一半,他就潦草收?qǐng)觥Q莩鼋Y(jié)束,有兩個(gè)女生還專門跑過(guò)去安慰他,給他說(shuō)加油,“沒說(shuō)還好,說(shuō)了我更尷尬地想‘死’,后來(lái)起碼花了四五場(chǎng)演出的時(shí)間,我才調(diào)整過(guò)來(lái)心態(tài),敢再上臺(tái),也不是畏懼,就是覺得丟人,這次經(jīng)歷是對(duì)心理的一次嚴(yán)重打擊”。
想要在業(yè)務(wù)上更進(jìn)一步,大多數(shù)脫口秀演員都得靠自己摸索,方式多種多樣,比如觀摩有名脫口秀演員的演出視頻,學(xué)習(xí)他們文本的邏輯、結(jié)構(gòu)和框架,再自己創(chuàng)作,但真正想要精進(jìn),還是需要在舞臺(tái)上的磨練,根據(jù)觀眾的反饋再調(diào)整文本和表演。
入行以來(lái),楊梅和媚兒都曾有過(guò)猶豫的時(shí)刻。
如果繼續(xù)做之前的那份影視營(yíng)銷工作,楊梅可能像她大多數(shù)同事一樣,已經(jīng)做到了公司的中高層,她不是沒有想過(guò)放棄,但她深知自己是個(gè)以興趣為驅(qū)動(dòng)力的人,“如果我不做這個(gè),我心里就不得勁”。
“公司除了創(chuàng)始人和我,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幾歲,包括整個(gè)重慶的脫口秀,大多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因?yàn)槟壳懊摽谛阒饕€是在大學(xué)生團(tuán)隊(duì)以及年輕人團(tuán)體中比較流行。”媚兒笑說(shuō),“我有時(shí)候懷疑自己這么大年紀(jì)搞這么時(shí)髦的東西,到底行不行,但最終還是興趣讓我堅(jiān)持下來(lái)。”
《脫口秀大會(huì)》舉辦到第四季,選手從一開始的純喜劇人出身逐漸多樣化到各行各業(yè),對(duì)這個(gè)變化,楊梅覺得很正常。在她看來(lái),有三類人講喜劇天生有優(yōu)勢(shì),一類是父母從事表演或喜劇相關(guān)的職業(yè),一類是本人之前從事過(guò)表達(dá)相關(guān)的職業(yè),比如媚兒,還有一類就是有深厚社會(huì)閱歷的人,比如《脫口秀大會(huì)》出現(xiàn)的“癌癥生物學(xué)博士”或“交警”,“根源在于脫口秀這個(gè)行業(yè),它的屬性是讓大家表達(dá)自我,所以說(shuō)每個(gè)行業(yè)每個(gè)人都有機(jī)會(huì)成為脫口秀演員,就看你下的功夫和你個(gè)人的經(jīng)歷。”
一場(chǎng)演出100元
“父母覺得我像紅白喜事的表演者”
進(jìn)入脫口秀行業(yè)簡(jiǎn)單,但想長(zhǎng)久堅(jiān)持下去卻很難,首當(dāng)其沖就是收入。
做影視營(yíng)銷工作的時(shí)候,楊梅每個(gè)月收入過(guò)萬(wàn),但轉(zhuǎn)行做脫口秀演員的時(shí)候,因?yàn)閯側(cè)胄校摽谛闼竭€未達(dá)到商演的標(biāo)準(zhǔn),沒有俱樂部邀請(qǐng),也就沒有收入,她需要接影視營(yíng)銷私活來(lái)養(yǎng)活自己。“本來(lái)是想辭掉工作之后好好打磨脫口秀內(nèi)容,誰(shuí)知道離職后面臨經(jīng)濟(jì)壓力,反而沒有時(shí)間好好做內(nèi)容了”。
好在隨著脫口秀水平越來(lái)越高,楊梅也接到了俱樂部邀約。“北京這邊最初講是一兩百元一場(chǎng),甚至不要錢,后面會(huì)根據(jù)你的水平、名氣、市場(chǎng)行情慢慢上漲,200到800元一場(chǎng)都有,不停在變化。”
楊梅這樣的情況在脫口秀行業(yè)比比皆是,大多數(shù)人如她一樣憑借著興趣闖入這個(gè)行業(yè),但因?yàn)樾氯俗髌凡怀墒欤词怪v開放麥,也可能沒有收入,只有當(dāng)作品成熟一些時(shí),才能拿到為數(shù)不多的報(bào)酬,很多人在成為全職脫口秀演員之前都會(huì)兼職試煉,短則一兩個(gè)月,長(zhǎng)則一兩年,這期間的月收入大概在一兩千元左右。
遠(yuǎn)在重慶的媚兒和郎飛鴻也一樣。媚兒剛?cè)胄械臅r(shí)候就一邊說(shuō)脫口秀,一邊做微商賺錢維持生計(jì),而如今還未簽約公司的郎飛鴻用“每個(gè)時(shí)期都很窘迫,如今依然是”這樣的話來(lái)形容自己的收入,目前他幾乎每天都有演出,但因?yàn)闆]有簽約公司,月收入才五六千元,“之后簽約公司后,可能有小一萬(wàn)吧”。
據(jù)悉,目前北京普通全職脫口秀演員的收入大概在一萬(wàn)元左右。
不過(guò)脫口秀跟影視行業(yè)一樣,不同咖位的藝人,收入也有天壤之別。
“商業(yè)演出的話,普通脫口秀演員一場(chǎng)五六百元,但有名氣的脫口秀演員,可能15-30分鐘之間可以拿到幾萬(wàn)元。”郎飛鴻透露。
本來(lái)隨著《脫口秀大會(huì)》第四季的熱播,線下演出市場(chǎng)也越來(lái)越火熱,但疫情的反復(fù),讓脫口秀演員的工作也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受疫情影響,重慶地區(qū)8月份的線下演出全都暫停,媚兒只能去接一些小的商業(yè)活動(dòng),“就你在上面講,顧客在下面吃,這種現(xiàn)場(chǎng)效果沒法保證,心里其實(shí)蠻不舒服,但是沒有辦法,常規(guī)演出都取消掉了,為了生活只能講。”
郎飛鴻本來(lái)最近要簽約重慶數(shù)一數(shù)二的公司,受疫情影響還不知道會(huì)不會(huì)有變化,線下演出做不了,收入影響是必然的,“現(xiàn)在我天天除了吃就是睡”,加上沒有簽約公司,無(wú)人給他發(fā)基礎(chǔ)工資,他目前只能吃老本,他擔(dān)心疫情戰(zhàn)線拉得太長(zhǎng),“就算復(fù)工了,可能也沒人來(lái)看”。
除了收入,很多脫口秀演員最大阻力來(lái)自于父母對(duì)這份職業(yè)的不看好。
“我父母覺得我講脫口秀就是不務(wù)正業(yè),他們把我當(dāng)做那種在紅白喜事上敲鑼打鼓的樂隊(duì)。”郎飛鴻笑說(shuō),“不過(guò)我就是要飯,我父母也不會(huì)說(shuō),只要我不說(shuō)父母雙亡就行。”此前他參加《中國(guó)好聲音》的時(shí)候,特意選了一首歌唱給父母,結(jié)果他們那天都忘了去,一個(gè)在打麻將,一個(gè)去釣魚。
相比郎飛鴻父母“放養(yǎng)式開明”,媚兒的父母更為嚴(yán)厲一些。此前她的工作屬于央企,在父母眼中收入穩(wěn)定又體面,很好找男朋友,但媚兒不喜歡那種一眼就能看到頭的工作,毅然決然辭了工作,“到現(xiàn)在他們還在勸我回去,但我聽不進(jìn)去”。說(shuō)脫口秀兩年了,媚兒也沒敢請(qǐng)父母去看,“我有一些跟我媽媽碰撞出的段子,我怕她看了,心臟受不了。”
脫口秀劇場(chǎng)里的“人設(shè)”
當(dāng)“戀愛大師”之余,我最擅長(zhǎng)講“窮”
在脫口秀舞臺(tái)上,幾乎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人設(shè)”。
比如何廣智的“窮”,趙曉卉的“車間女工”,王建國(guó)的“諧音梗”,王勉的“吉他”,楊笠的“女權(quán)”等,這“人設(shè)”可能來(lái)自于脫口秀演員的人生經(jīng)歷,也可能生發(fā)于他們的個(gè)性,但無(wú)論是哪種人設(shè),都是站在舞臺(tái)上的一種醒目標(biāo)識(shí),能夠讓他們被觀眾快速記住。
線下脫口秀演員大多也不例外。
郎飛鴻身上的標(biāo)簽是“正宗重慶崽兒”,月收入幾千塊的他,笑侃自己除了當(dāng)“戀愛大師”,最擅長(zhǎng)講窮,比如如何使用花唄,怎么網(wǎng)絡(luò)貸款。而34歲的媚兒,最醒目的人設(shè)就是“大齡單身女青年”,她的很多段子都來(lái)自于“社會(huì)上對(duì)大齡未婚女青年的一些看法”。
“脫口秀跟其他喜劇形式不太一樣,其他喜劇表演,你演的不是自己,而是角色,但脫口秀帶有非常強(qiáng)烈的自我色彩,演員講的段子基本上都是自己生活中的經(jīng)歷加工的。”媚兒說(shuō)道,“而且脫口秀也跟以前我們了解的某些喜劇不一樣,比如東北二人轉(zhuǎn)之類,他們可能需要扮丑來(lái)達(dá)到娛樂大眾的效果,但脫口秀只需要做自己。”
當(dāng)自己的生活沒有那么多靈感時(shí),就需要脫口秀演員盡量觀察生活。媚兒透露自己平時(shí)會(huì)多看看網(wǎng)上發(fā)生的事情,也會(huì)在講脫口秀的時(shí)候,跟觀眾碰撞出一些火花,“還有平時(shí)出去,正常人可能都在地鐵或公交車上玩手機(jī),我不玩手機(jī),我會(huì)看一下周圍人他們的狀態(tài),觀察加以提煉,可能就是我的段子。”
相比綜藝節(jié)目中脫口秀演員更旗幟鮮明,更貼近社會(huì)熱點(diǎn),也更便于傳播的“人設(shè)”,楊梅認(rèn)為,線下演員所謂的“人設(shè)”,更多是基于自己想要表達(dá)的思想,“比如我最近正在談戀愛,那可能這一階段我就會(huì)主要講這個(gè)話題,有的演員很有抱負(fù),想為女性或弱勢(shì)群體發(fā)聲,他們可能就會(huì)主要講這類話題。”

《脫口秀大會(huì)》選手江梓浩曾調(diào)侃自己家庭背景又正常,父母健康又活潑、從來(lái)不離婚,也從來(lái)不打他,所以他一點(diǎn)“素材”都沒有。另一名脫口秀演員楊曉卉也曾笑說(shuō),“我是為了抱怨生活來(lái)到這里,但他們告訴我這就是脫口秀”。
他們的話雖是玩笑話,但也道出一絲真相——有經(jīng)歷的人有更多素材,也更容易講好脫口秀。
“脫口秀創(chuàng)作的一大來(lái)源是負(fù)面情緒,當(dāng)然,一個(gè)人聰明、善良、幽默也能寫出很好笑的段子,但確實(shí)大比例的脫口秀還是通過(guò)負(fù)面情緒去推動(dòng),就是你寫一個(gè)段子,它其實(shí)是在給觀眾制造優(yōu)越感,通過(guò)加工你一些不開心的事情,讓觀眾產(chǎn)生優(yōu)越感而笑出來(lái)。”楊梅剖析道,“如果一個(gè)人在臺(tái)上講自己過(guò)得有多好,其實(shí)不那么討喜,黃西老師的脫口秀有凡爾賽的地方,但落腳點(diǎn)是‘我在低谷等你們’,最終,他還是把自己的姿態(tài)放得很低。確實(shí),苦難會(huì)變成你的財(cái)富,變成相對(duì)更好加工的素材,最終變成你的段子。”
在這方面,楊梅有著和江梓浩同樣的煩惱,她的家庭幸福,父母開明,對(duì)她傾注了很多的愛,所以她寫段子的時(shí)候,“在挖掘情緒這方面花了挺久時(shí)間”。不過(guò)因?yàn)樵?jīng)有過(guò)文案策劃的經(jīng)歷,所以她在脫口秀文本上常常會(huì)有很多巧思,為了保證內(nèi)容持續(xù)更新,她像大學(xué)時(shí)期一樣和朋友組成學(xué)習(xí)小組,“每周有固定的時(shí)間去討論內(nèi)容,互相激勵(lì),讓自己有持續(xù)的內(nèi)容產(chǎn)出”。
從贈(zèng)票沒人來(lái)到場(chǎng)場(chǎng)爆滿
“脫口秀是對(duì)生活的治愈”
隨著脫口秀行業(yè)越來(lái)越火熱,在入行三年多之后,楊梅成立了一家自己的俱樂部,靠譜能干的合伙人幫她做運(yùn)營(yíng),讓她終于解決了在面包和夢(mèng)想之間互相拉扯的難題,專心做內(nèi)容。
回想剛?cè)胄袝r(shí),整個(gè)行業(yè)在楊梅的印象中就一個(gè)“窮”字。
最慘的時(shí)候,臺(tái)上有六七個(gè)演員,臺(tái)下就一個(gè)觀眾,等到楊梅入行的時(shí)候,情況稍微有所好轉(zhuǎn),臺(tái)下可能有個(gè)四五個(gè)觀眾,但一個(gè)脫口秀演員要辦專場(chǎng)也是很困難的事情,即使他給別人贈(zèng)票,對(duì)方也不一定會(huì)去,因?yàn)槟菚r(shí)候很多人并不了解脫口秀,哪怕是贈(zèng)票,他們一想到還要出門,還要打車,可能就放棄了,“但這兩年,尤其是今年,能明顯感覺到觀眾越來(lái)越多了,脫口秀也納入了年輕人跟朋友相約時(shí)的一個(gè)選擇范圍之內(nèi)。”
觀看人數(shù)多了,票價(jià)自然也上去了。楊梅透露,2017年左右的時(shí)候,常規(guī)的脫口秀門票大概在50—80元之間,而如今有所升高,在80—150元之間,“當(dāng)然,如果是特別有名的廠牌,有名的脫口秀演員,而且是那種千人劇場(chǎng)的話,可能他第一排的票價(jià)就有一千多元。”
線下脫口秀行業(yè)的火熱,郎飛鴻和媚兒也明顯察覺到了。
“以前脫口秀演員去講開放麥,門票可能就19.9元、29.9元,但依然無(wú)人問津。”媚兒透露,“這兩年,隨著《脫口秀大會(huì)》越來(lái)越火,脫口秀也開始廣為人知,我們劇場(chǎng)脫口秀門票68元,除了周一周二不演出,其他時(shí)間小一百人的場(chǎng)子都是賣滿了的。”
“自從重慶出過(guò)《奇葩說(shuō)》和《脫口秀大會(huì)》的選手,明顯感覺線下脫口秀行業(yè)火了很多。”郎飛鴻直言,“以前主營(yíng)相聲的一些團(tuán)體也會(huì)加上脫口秀這個(gè)業(yè)務(wù),有些年輕人可能不了解這個(gè)廠牌,也不知道演員是誰(shuí),但一些購(gòu)票網(wǎng)站上只要有脫口秀這三個(gè)字,購(gòu)票數(shù)量就會(huì)猛增。”
不過(guò)楊梅也發(fā)現(xiàn),脫口秀的這種火,并非常態(tài),更像是一種風(fēng)潮,因?yàn)楫?dāng)她在線下跟觀眾互動(dòng)時(shí),問有多少人是第一次來(lái)看脫口秀時(shí),每次都有很多人舉手。
市場(chǎng)火了,脫口秀演員短缺的問題也挺嚴(yán)重。“北京有十多家廠牌,但全職脫口秀演員可能就那二三十個(gè),經(jīng)常周末就會(huì)出現(xiàn)盤子很多,但菜不夠的現(xiàn)象,脫口秀演員就會(huì)趕場(chǎng),但演員的內(nèi)容更新頻率大多沒有那么高,有時(shí)候可能他們一個(gè)月、兩個(gè)月,甚至三個(gè)月講得都是一樣的內(nèi)容。”
這個(gè)問題,媚兒也意識(shí)到了。她有時(shí)候也會(huì)去看其他脫口秀演員的表演,會(huì)發(fā)現(xiàn)脫口秀市場(chǎng)的演出參差不齊,有的脫口秀演員的水平并沒有達(dá)到可以開演的標(biāo)準(zhǔn),但他們依然在演。“這是明顯地割韭菜行為,有些觀眾可能看了就完了,但我覺得這個(gè)不太好,不利于行業(yè)的發(fā)展。”
無(wú)奈也好,惋惜也好,可能這就是脫口秀行業(yè)在從零到一時(shí)需要面臨的問題。好的一面是,行業(yè)的快速發(fā)展,給脫口秀演員帶來(lái)了更多上升通道。
“線下可以做演出,積累了足夠的內(nèi)容就可以走線上。”楊梅介紹道,“一種是自己做社交賬號(hào),積累足夠的粉絲接商務(wù),另一種是參加線上綜藝,或一些小節(jié)目,獲取流量進(jìn)而變現(xiàn),再就是做俱樂部的簽約脫口秀演員,俱樂部可以幫忙對(duì)接演出和商務(wù),或者做管理者,有很多種方式。”
談及未來(lái)的職業(yè)規(guī)劃,媚兒透露,自己今年參加了《奇葩說(shuō)》的辯論,已經(jīng)通過(guò)了兩輪,如果順利的話,她會(huì)一直辯論下去。此外她希望能夠再豐富豐富自己的內(nèi)容,“明年想辦法在重慶開一個(gè)專場(chǎng)就OK了”。
而郎飛鴻正在等待疫情好轉(zhuǎn),這樣他就可以與已經(jīng)談妥的公司順利簽約,這樣他的薪酬不但可以提高,公司還會(huì)保證他的演出次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我會(huì)做一些自媒體,也會(huì)去嘗試新的東西,比如舞臺(tái)劇,當(dāng)然,之后也會(huì)考慮去參加《奇葩說(shuō)》和《脫口秀大會(huì)》。”這是很多脫口秀演員都?jí)粝氲巧系奈枧_(tái)。
成長(zhǎng)為俱樂部老板的楊梅,她已經(jīng)替自己做好了未來(lái)一年的規(guī)劃。個(gè)人方面,她打算跟自己一個(gè)要好的脫口秀演員朋友一起做一個(gè)雙拼脫口秀專場(chǎng),公司層面,她的目標(biāo)是擴(kuò)大場(chǎng)地賣出更多的票,“今年打算再開一個(gè)俱樂部酒吧,已經(jīng)拉到投資了,正在裝修,希望每個(gè)月能夠售出5000張左右的票。”
欣欣向榮的未來(lái)規(guī)劃中,楊梅回憶起入行以來(lái)印象最深的一場(chǎng)演出。
那是年初的時(shí)候,疫情剛好轉(zhuǎn),演出慢慢開放,很多觀眾戴著口罩來(lái)看脫口秀,楊梅那天負(fù)責(zé)統(tǒng)籌,站在觀眾席后面靜靜看著臺(tái)上的表演。在此之前的那段時(shí)間,各種疫情新聞讓人很壓抑,但在那場(chǎng)演出里,演員表演得很賣力,觀眾笑得也很大聲,“在那一刻,我覺得做脫口秀這個(gè)事情是有意義的,最起碼在那一個(gè)半小時(shí)里,可以讓大家忘記煩惱,暢快地笑出來(lái),這是一種對(duì)生活的治愈。”
標(biāo)簽: 脫口秀大會(huì) 脫口秀 演員 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