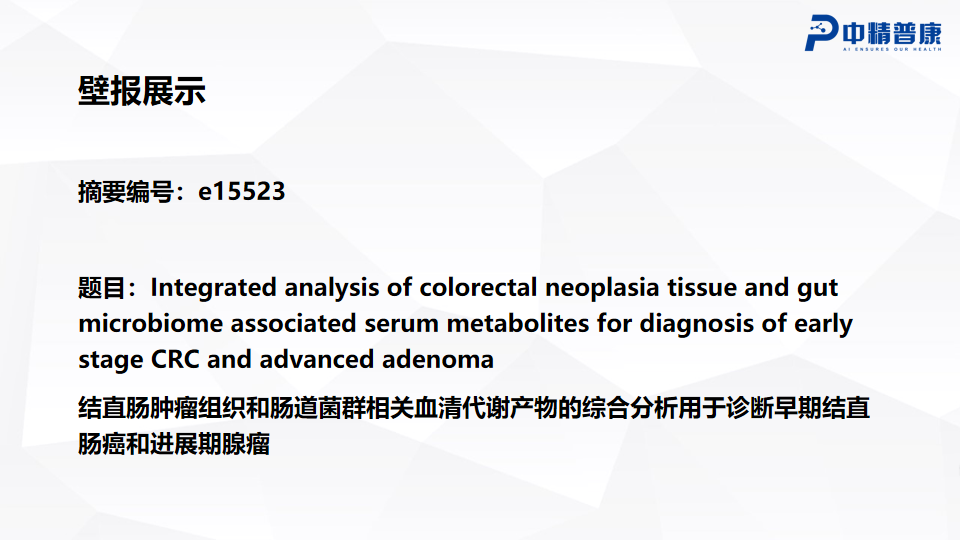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底線》:現實溫度的成功與倫理化策略的失靈3天天新動態(tài)
趙瑞君
縱覽近年來國產法治題材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底線》無疑是表現亮眼的一部。該劇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指導,用40集的長度匯集了近年來極具代表性的真實案件和社會現象。9月在湖南衛(wèi)視、芒果TV等平臺播出以來,《底線》被不少觀眾稱為“法治題材劇集新標桿”,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出圈:微博、抖音等平臺上,有人嚴肅討論與劇集相關的社會議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底線》收獲好評或許是一種必然。在大量職場劇刻板塑造精英、劇情懸浮的當下,《底線》與現實之間的聯(lián)結顯得頗具溫度,接地氣的職場書寫讓劇中“專業(yè)性”的部分亦能得以落地。但同時,部分觀眾的質疑又讓人不得不略顯“苛刻”地看待這部作品:在觀眾審美習慣逐漸改變的今天,在與“法理”同臺競技的劇集中,道德感召和倫理敘事如何適度展現?
去精英化:職場劇的日常美學
在近年來的國產劇發(fā)展中,不少電視劇類型成功實現突圍,懸疑劇、古裝劇頻現爆款。與之相比,職場劇則低調許多,盡管有不少以職場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但大多因行業(yè)性不強、劇情不真實而遭到詬病。而在犯罪、刑偵等題材的電視劇中,主角較多為警察,劇情追求驚險刺激,人物自帶光環(huán)。
在此背景下,《底線》的取材就十分注重“取巧”。該劇表現的是此前在國產劇中出鏡較少的法院工作人員,但對觀眾而言,這一群體非但不陌生,而且回應著不少中國觀眾的審美期待。長久以來,民眾對于公正的向往和對清官的企盼,使各類“包公戲”輪番上演、經久不衰,而法官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無疑是維護現代社會正義的包青天。但具有進步意義的是,《底線》并沒有塑造披荊斬棘、全知全能的法官形象,而是回歸生活,平實講述基層法院工作人員為民眾調解矛盾糾紛的日常。
這種“日常感”在男主人公方遠身上得以集中體現。劇中,鏡頭多次表現方遠坐地鐵上下班、地攤上吃早飯,這樣的畫面重復出現,加強了劇集的煙火氣和真實感。在調解糾紛時,方遠并不會運用身份優(yōu)勢充當說教者和審判者,而是在聊家長里短之間,幫當事人解開心結。同時,該劇并不將職業(yè)神秘化或刻意拔高,在整部劇中,方遠積極爭取升職是一大敘事動力,而在此過程中引出的主人公兢兢業(yè)業(yè)工作卻遭當事人惡意投訴,體現了法律工作者樂觀背后的無奈。
當然,《底線》中的職場并不完全聚焦于一兩位主人公,而是借案件的改換,呈現真實可信的人物群像。雖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法院工作人員,角色之間卻有鮮明的個體差異:葉芯被調侃為“教條姐”,但她看似激進的思想常在關鍵時刻點醒當事人;王秀芳是法院里的老前輩,但常因為觀念差異與葉芯發(fā)生爭執(zhí);年輕法官鐘媛媛看似溫婉,但時不時開懟領導信奉的“加班文化”……以群像為核心,劇集展現了法院人的努力、互助,也真實呈現了新老從業(yè)者的觀念差異與彌合。
現實主義:時代的新聲與詰問
除了人物回歸“日常”,劇情設定也著眼時代與現實,司法建設新成就和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比較有效地與敘事縫合。這是《底線》可看性較高的原因。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法院工作和民眾維權的方式亦發(fā)生了改變,但普通群眾對其具體情況往往所知甚少。在《底線》中,開篇便展現法官們對“電子卷宗”的討論,隨著劇情發(fā)展,開庭直播、跨域立案、云調解等新興事物逐一被介紹。聚焦法院內部之余,鏡頭往往會穿插法庭外觀看庭審直播的觀眾畫面,他們可能是事件當事人的同行,也可能是出于質樸的關注和同情,在畫面穿插之間,原本“置身事外”的觀眾被納入場內。這些細節(jié)看似篇幅較少、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劇中圍觀群眾的視角和觀眾的觀劇視角往往會產生重合——在一種共鳴中,觀眾不僅了解了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更是對法治建設的未來充滿信心。
當然,《底線》并不是一部死板的說教電視劇,能受到不少觀眾的喜愛,是因為該劇秉持著現實主義的書寫原則,將近年來大眾關注的熱點現象、社會問題有效網羅。例如,在“主播猝死案”中,法官們既討論了“資本追逐利益”的弊病,也無奈地感嘆“父母隨機分配”;在“唐嘯云弒母案”和校園霸凌事件的講述中,喪偶式育兒、家庭教育方式失當等問題得以多重呈現。值得注意的是,劇中對女性處境兩難的呈現十分真實,女性的繼承權問題、就業(yè)難問題、遭遇污名化的處境在劇中皆有展現。可貴的是,事件當事人并未被塑造成爽劇式的“大女主”,女銷售李芳凝工作能力強、衣著考究,但面臨的卻是異性同事得寸進尺的騷擾;公司老板娘吳華年輕時與丈夫共同創(chuàng)業(yè),中年想再回職場時卻不被丈夫理解。此類事件的呈現往往是一波三折,這也讓觀眾再次正視:維護女性權益,改變性別偏見,是否依然道阻且長?
倫理色彩:觀眾如何看待法理與情理
除了著眼現實、引起共鳴的方面,《底線》播出后引起的爭議也不容忽視。該劇的另一名稱叫做“庭前無訟”,正如這一名稱所暗含的,劇中法官們的工作策略并非“以法理震懾”,而是更加提倡“在道德上說服”,讓當事人心甘情愿“遵守公序良俗”。在劇情上加強道德感召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融合了中國觀眾最為熟稔的倫理敘述,切實帶來了不少淚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道德感召是否有效地被大多數觀眾接受?
正如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論斷,大眾除了認同、協(xié)商式地對文本進行接收,亦有可能出現對抗式解碼,即“完全理解事件中給出的字面意思和內涵意義的變形,但決定用一種與之相反的方式進行解碼”。回歸《底線》,該劇目前所遭到的質疑或許也有此種意味,過度的道德感召削弱了法理探討的深度,也讓觀眾產生了某種審美疲勞。例如在真實事件的改編中,江歌案中的母親被改為丈夫,人物關系的變化直接鉗制了敘事的走向;而在改編“貨拉拉跳車事件”時,司機被強行加上孝子身份,改編者或許是想突出勞動者的不易和司機粗獷外表下的細膩,但這種做法卻未被各方買賬。
本文并不否認《底線》的質量,劇集對社會現實和熱點事件的聚焦無疑是極具勇氣的。但在改編過程中,也應看到和尊重當下觀眾的審美蛻變。熱點事件中的現實意義和法理啟發(fā)是珍貴的原材料,或許不用泛濫的倫理敘事取而代之,也能在觀感上達到更好的效果,并進一步引導觀眾提高公民意識。
標簽: 敘事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