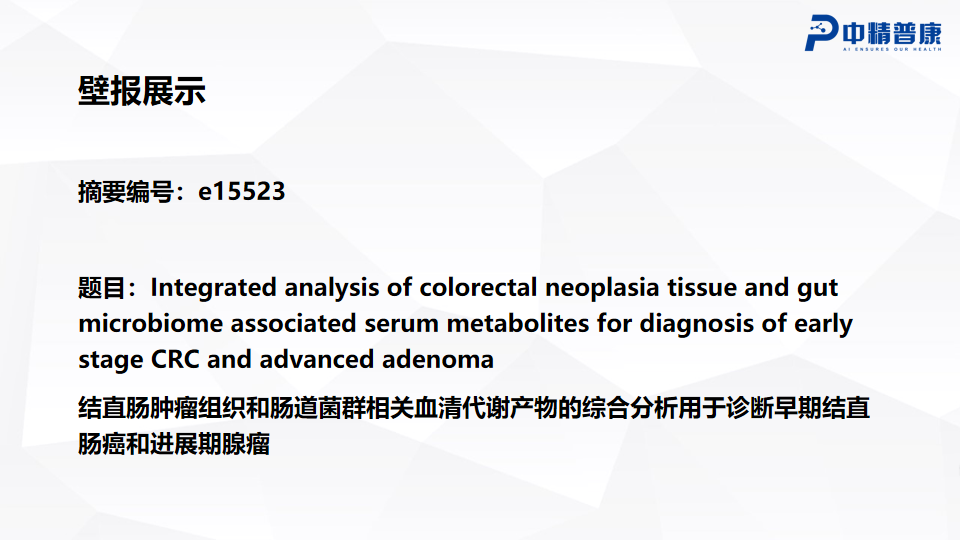對萬瑪才旦的慎重情感
◎巫昂(作家)
5月8日下午,多方信源證實,中國藏族藝術家萬瑪才旦當日凌晨逝世于西藏,享年53歲。
 (資料圖)
(資料圖)
萬瑪才旦,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國著名導演、編劇、作家、制作人。
今年3月底,萬瑪才旦自編自導的新片《陌生人》剛剛拍攝完成,目前正在后期制作階段。7日傍晚五點多,萬瑪才旦還發了新的朋友圈——配圖是藏族導演格杰白瑪電影《禮物》的海報和獲獎證書,“祝賀年輕的電影人!”這是萬瑪才旦留給世間最后的祝福。
自2005年自編自導《靜靜的嘛呢石》始,萬瑪才旦就是國內最活躍的藏地導演,持續貢獻了《塔洛》《撞死一只羊》《氣球》等以藏區為背景的電影。除了作為導演、編劇持續創作,萬瑪才旦也是一位高產的作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堅持小說創作,去年才出版了新的短篇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
相較于個人創作成就,萬瑪才旦對藏地電影甚至中國電影更大的貢獻是,激勵并引導了一批藏族年輕人走上電影創作的道路。他是《扎旺的雨靴》和《一個和四個》的制片人和監制,他帶領拉加華、久美成列、金巴等一批藏區青年電影人一起,掀起“藏地新浪潮”。
早上五點五十七分,我起床,取了一杯溫水,徑直在書桌前坐下打開電腦。二十幾年間,我殘存的寫字陣地居然是“逝者”欄目,寫的居然是我以為可以再活四五十年、拍出伯格曼那么長的電影清單、寫出比卡佛更多得多的短篇小說的人。?——巫昂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我們的往來之初,是2021年年底,大屏幕上《撞死了一只羊》的藏族男人變成了加了微信的親切的朋友。我給他寄了我當時新出的書,三天后他回復“書收到了,回去拜讀!”這是一個周全而忙碌的人,當時我有一個基本印象。又過了半年左右,他讓我給他地址,要讓出版社給我寄他新出的書,那應該就是他在中信大方出的《故事只講了一半》,一本新的短篇小說集。此前我已經讀過了《烏金的牙齒》。
過了一個月左右,他在夜里十點多跟我說:“今晚聽了您講卡佛,挺有收獲的。”那是我在新浪連麥的欄目“巫聊”的第一期。講了兩期卡佛,我在連麥的嘉賓席上確實赫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一晚上靜靜地掛在那里。于是有了一段關于卡佛的交談,他還知道我有個寫作班,我接下來那周還要講卡佛,他居然又如約來聽,還是安安靜靜地在嘉賓席上坐著。那期間,我們還聊了電影與小說,寫小說對于拍電影有好處等話題,像兩個認真的人在聊認真的事。第二天,我就開始讀《故事只講了一半》。
萬瑪才旦是個怎樣的人呢?連日來朋友圈刷屏的他變成了逝者的消息,人們往往說他儒雅溫厚。有一位朋友說他的周全和禮貌,讓他過于內耗了。他有著作為導演來說過于俊美的容顏,做演員也絲毫不差,他在任何場合出現的照片都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觀者如是,我也并不例外。我們因著他所喜愛的作家卡佛開始的往復微信里,充滿了他的溫暖與溫情。
我通常都有將喜歡的作家的書盡數收集齊的習慣。當我讀了一多半《故事只講了一半》,跟他說打算收集齊他的書,他竟然說要寄給我。因為家中幾個小說集重復的比較多,樸素的理由。這是讓人十分驚詫的周全,我隱約覺得這會耗費他非常多的心神。即便作為一位小說家,他的小說里有一種哈金或者說卡佛式的樸素的冷幽默。
接下來,我度過了全面了解萬瑪才旦作品的一個月。讀完了差不多能找到的他的所有的小說,看完了他所有的電影。周全如他,電影的所有鏈接都是他挨個兒發給我的。
大昭寺浩浩蕩蕩的酥油燈
家里來了客人睡在我床上,我與母親同睡。所以,暫時沒有一個被窩,甚至一個衛生間可以掩蓋我的哀慟。事實上,過去的七十二小時,我但凡不工作、不與人交談,眼淚便充滿了眼眶。需要每隔幾個小時便痛哭一場,才能維續下一時段具體的生活。愛他的普通人如我也未能免俗,死,是永遠必須去相信的生者自身提前的死訊。我的心從今往后將永遠缺失一塊,且沒有酥油燈的光亮照耀。他的死撞死了我的生。
在這篇文章里,我想不僅僅寫他之于中國電影、中國小說的不可或缺的關系的宏大敘事。我想說,這里面最大的遺憾是,一位天才創作者、一位真誠質樸而又無比豐富的人,經過漫長的歲月,終于迎來了屬于他的時間,然而天地不仁。
他的電影和小說都不僅僅屬于這個國度,他這個人更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一位真正的作者導演的典范。自己會寫小說寫原創劇本,自己有著執拗而又深入的視覺和哲學思考。《尋找智美更登》里那位終于放下執念的女孩,還有《氣球》中也終于放過了自己的女孩,讓他擁有了不只是男性的視角。無疑,他人格中的溫暖和溫情,造就了這種對于電影中人的提醒和勸告。
從讀完、看完他所有小說和電影之后的2022年5月底,我們就相約做一次有意思的對談,在新浪微博連麥,那是“巫聊”的第五期(之后便停更至今)。我自己當即設計了海報,跟他約了時間,是6月17日。
與此同時,他看到我朋友圈在寫一個小說叫作《跟別人的男朋友一起逛公園》。我說為此逛到了第二個別人的男朋友了,他問我這個小說寫完了沒有,讓我寫完了給他看看,原話是——“做個洪尚秀式的文藝電影應該不錯”。于是,在卡佛和哈金之外,我們達成了第三個一致,都喜歡洪尚秀的電影。他對我這個小說的期待是:“故事有趣一點,能涉及兩性關系的一些深層問題就好”。那段時間,我們聊過馬爾克斯的《巨翅老人》,因為他讀了我的另外一個短篇《戰馬希恩》。我們都認為寫小說是需要創新的,要有一種帶著形式和美的活力。
驚人的深刻和勇敢
他的《故事只講了一半》那本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歡的是《水果硬糖》。那里面也有一位非常獨特、迷人的女性角色——那位老母親。她的愛超過了對于是非的判斷,她有一種對于愛的超越然而天然自得的認識與實踐。他說自己也是最喜歡這一篇,還想著要有一天把它改編成電影。當時我暢想著去拉薩看這部電影,走出影院的時刻,大昭寺迎來它的晚課——一定有這種情境,那些酥油燈為了死去的亡靈超度;一定沒有那種預知,一年不到之后,它要為《水果硬糖》的父親而燃起。
我替他高興,多么幸福啊,把自己在一本書中最喜愛的篇目,在大屏幕上再演繹一遍。我替他構思,永遠不存在的那個假定性未來的某一天,他會不會自己去包個獨自一人的下午場,在黑暗中對著那位老母親永不變更的愛落淚。
另一個他的電影中我時常會想起的場景是《老狗》的結尾。所謂“老狗”是藏獒,一度是內地豪富們懷錢不遇的“奇貨”,但是對于片中藏地小鎮上的那位老者,他的藏獒是他的親人。有人想方設法要盜走這條老狗,變成他們獲利的商品。老者最終決定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又是下午),親自將老狗帶到荒僻的草原上,將它親手勒死。
萬瑪才旦在跟我的對談中,也特地談起了這場戲。這部電影是順時間拍攝的,整個劇組都不知道結局如是。那天拍完,大家集體陷入了難以言喻的痛苦和壓抑之中。這讓我想起了史蒂芬·金小說改編的電影《霧》,那個被霧中怪物一路追趕的男人,最終選擇了親自用槍擊斃了妻兒。因為深切的愛與深刻的親密,終結所愛者的生命,免其落入其他人或者怪物之手,遭到最不堪的凌辱。這里面有一種極大、極殘忍的悖論在,一種自我殘忍。老狗死去后老者的存在狀態,和那位擊斃妻兒的中年男人一樣,將要猶如喪家之犬,余生都要在難以入眠的煎熬中度過。
這場戲,讓我感受到了萬瑪才旦驚人的深刻和勇敢。在他猝然離世后,諸君的懷念文章里都提到了他的知識分子氣質,我覺得這場戲,就充分體現了他的知識分子式的深切思考和體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到了萬瑪才旦這里,延伸到了“老吾老以及老之狗”,萬物有靈何況老狗。
那個靜穆空曠的藏地草場的下午,我想象著本來如度假一樣輕松拍戲的劇組諸君,在獵獵的風中沉默不語;我想象坐在監控屏前沉默不語的萬瑪,我想象他那一刻的緘默猶如他之于那片土地、那片高遠天空的緘默,那些他無法用言語、文字和畫面說出來的無窮無盡的話,那些畫外的大音希聲。
所有擦肩而過的那些時間
從對談之后,就開始了漫長的跟萬瑪才旦的見面之約,約著要好好聊聊天,預計無外乎電影和文學吧。我忍著無邊無際的傷心翻看我們約見而又擦肩而過的那些時間——
2022年的7月,我到了杭州,他在次日跟我說:“到杭州了嗎?我剛到拉薩。”那是疫情還未完結的時間,我本來要去天津參加芒種詩歌節,結果臨了取消了,我便盤桓于杭州。
當月月底他要去First影展,問我是不是有時間,有時間的話可以去。我本來想那段時間去甘肅柳園做下一個長篇的調研,查了查地理方位,離西寧已經很近了,從敦煌飛到西寧的曹家堡機場,機票不過五百來塊。
這之后他在北京的時候我在臺州,我預告說9月份之后會有半年在北京,他便說那就在北京見吧。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在不同的地點,我大概也是如此,所以,能對得上的時間很稀罕。
轉眼到了11月,北方的深秋,長三角的初秋,桂花已經開敗了,我重新回到臺州做宿寫作中心的線下寫作營。也在這期間,專門拿了一個下午(又又是下午),來給學生們精讀分析他的電影《塔洛》。那一片黑白的下午,竟然屬于一位有著小辮子會背誦《為人民服務》的牧羊人塔洛。羊走到了人間,羊迷失于人的陷阱,然后羊打算回到羊群里,然而羊已經不是羊了。羊最終被人宰殺,羊的血流在人同樣踏足的地上,這就是塔洛的故事。
這是不是萬瑪才旦自身命運的隱喻呢?我不敢貿然下此結論,因為他不是迷途的羔羊,他更像是一位摩西——一位帶領著藏地電影人和藏地電影突出重圍,試圖發出屬于藏語和藏地景象的聲音的那位有著悅耳神性的藏族名字的摩西。我用了這么多“的”,僅僅是想讓他的聲音在我身邊再盤旋一會兒。他那種悅耳和他那種柔和、他那種溫良和他那種廣闊和他那種迷人,我用了這么多的“和”,僅僅因為他有那么多美德、品質、天賦、操守、愛意,一兩個“和”無法概括。我用了那么多頓號,僅僅因為我已失去了巴別塔造就讓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分隔的語言,我和全體的我們一樣,已永失、痛失所愛。
2023年5月12日,北京東壩
標簽: